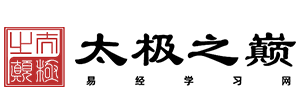[明]胡廣等敕纂《周易傳義大全?卷二十三》系辭下傳
繫辭下傳-[明]胡廣等敕纂《周易傳義大全?卷二十三》
周易傳義大全卷二十三明胡廣等撰繫辭下傳
八卦成列,象在其中矣。因而重之,爻在其中矣。
【重,直龍反】。
《本義》:成列,謂乾一、兌二、離三、震四、巽五、坎六、艮七、坤八之類(lèi)。象,謂卦之形體也。因而重之,謂各因一卦,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為六十四也。爻,六爻也。既重,而後卦有六爻也。
○朱子曰:八卦所以成列,乃是從太極、兩儀、四象漸次生出,以至於此。畫(huà)成之後,方見(jiàn)其有三才之象,非聖人因見(jiàn)三才,遂以己意思維,而連畫(huà)三爻以象之也。因而重之,亦是因八卦之已成,各就上面節(jié)次生出。若旋生逐爻,則更加三變,方成六十四卦。若併生全卦,則只用一變,便成六十四卦。雖有遲速之不同,然皆自然漸次生出,各有行列次第。畫(huà)成之後,然後見(jiàn)其可盡天下之變。不是聖人見(jiàn)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,然後別生計(jì)較,又幷畫(huà)上三爻以盡之也。此等皆是作易妙處。方其畫(huà)時(shí),雖是聖人,亦自不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。直是要人細(xì)心體認(rèn),不可草草立說(shuō)。
○問(wèn):八卦成列,只是說(shuō)乾兌離震巽坎艮坤,先生解云之類(lèi),如何?曰:所謂成列者,不止只論此橫圖。若乾南坤北,又是一列,所以云之類(lèi)。
○問(wèn):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,未說(shuō)到天地雷風(fēng)處否?曰:是。然八卦是一項(xiàng)看,象在其中,又是逐箇看。又問(wèn):成列是自一奇一耦畫(huà)到三畫(huà)處,其中逐一分,便有乾兌離震之象否?曰:是。
○南軒張氏曰:謂在其中者,言非自外至也。
○童溪王氏曰:聖人因象以設(shè)卦,則象在卦先;設(shè)卦以立象,則象在卦中。
系辭下傳?第一章
剛?cè)嵯嗤疲冊(cè)谄渲幸印@M辭焉而命之,動(dòng)在其中矣。
《本義》:剛?cè)嵯嗤疲载持儯鶃?lái)交錯(cuò),無(wú)不可見(jiàn)。聖人因其如此,而皆繫之辭,以命其吉兇,則占者所値當(dāng)動(dòng)之爻象,亦不出乎此矣。
《或問(wèn)》:變字是總卦爻有往來(lái)交錯(cuò)者言,動(dòng)字是專(zhuān)指占者所值當(dāng)動(dòng)底爻象而言否?
○朱子曰:變是就剛?cè)峤诲e(cuò)而成卦爻上言,動(dòng)是專(zhuān)主當(dāng)占之爻言。如二爻變,則占者以上爻為主,這上爻便是動(dòng)處。如五爻變,一爻不變,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為主,則這不變者便是動(dòng)處也。
○節(jié)齋蔡氏曰:剛?cè)嶝持w相推,謂剛推柔,柔推剛也。唯其相推,故能成其變。繫辭爻象之辭,即其變而命之,故能鼔其動(dòng)也。
吉兇悔吝者,生乎動(dòng)者也。
《本義》:吉兇悔吝,皆辭之所命也,然必因卦爻之動(dòng)而後見(jiàn)。
○柴氏中行曰:吉兇悔吝生乎動(dòng)者,主動(dòng)爻而言也。如情偽相感,遠(yuǎn)近相取,好惡相攻,皆是動(dòng)也。
○雲(yún)峰胡氏曰:八卦成列,即先天八卦橫圖也。因而重之,六十四卦橫圖也。象非特天地山澤之類(lèi),即八卦之畫(huà)成列,而象即在畫(huà)矣。未動(dòng)之先,有八卦之畫(huà),而未見(jiàn)八卦之交也。因而重之,爻在其中者,爻之為言交也。有交則有變,故剛?cè)嵯嗤疲冊(cè)谄渲小W兘y(tǒng)指卦爻而言,動(dòng)專(zhuān)指所值之變爻而言也。繫辭焉而命之,則文王、周公之易也。
○臨川吳氏曰:此承前篇卒章,言蓍卦之象辭變占。曰在其中者凡四:一象,二爻,三變,四動(dòng)。爻者辭也,動(dòng)則有吉兇悔吝之占焉。前篇?jiǎng)诱呱衅渥儯艘詣?dòng)屬占者,動(dòng)因變而得占也。
剛?cè)嵴撸⒈菊咭玻蛔兺ㄕ撸r(shí)者也。
【趣,七樹(shù)反】。
《本義》:一剛一柔,各有定位,自此而彼,變以從時(shí)。
○朱子曰:此兩句亦相對(duì)說(shuō)。剛?cè)嵴撸涥?yáng)之質(zhì),是移易不得之定體,故謂之本。若剛變?yōu)槿幔嶙優(yōu)閯偅闶亲兺ㄖ谩S?strong>曰:變通便只是其往來(lái)者。
○節(jié)齋蔡氏曰:剛?cè)嵴撸兺ㄖ倔w。變通者,剛?cè)嶂畷r(shí)用。
○雲(yún)峰胡氏曰:上繫曰剛?cè)嵴撸瑫円怪螅创怂^立本。曰變化者,進(jìn)退之象,即此所謂趣時(shí)。卦有卦之時(shí),爻有爻之時(shí)。立本者,天地之常經(jīng)。趣時(shí)者,古今之通義。
○臨川吳氏曰:剛?cè)嶂?huà),其體一定,如木本之植立。因蓍之變,其用相通,隨時(shí)所遇,趨而就之。剛或化柔,柔或化剛,此承剛?cè)嵯嗤疲冊(cè)谄渲兄Z(yǔ),而言蓍之變也。
吉兇者,貞勝者也。
《本義》:貞,正也,常也。物以其所正為常者也。天下之事,非吉?jiǎng)t兇,非兇則吉,常相勝而不已也。
○朱子曰:貞,只是說(shuō)他體處常常如此。
○貞,常也。隂陽(yáng)常只是箇相勝,如子以前便是夜勝晝,子以後便是晝勝夜。
○吉兇者,貞勝者也,這一句最好看。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,一箇吉便有一箇兇在後面來(lái),這兩箇不是一定往在裏底。物各有其所正為常,正是說(shuō)他當(dāng)然之理。
○進(jìn)齋徐氏曰:先言變動(dòng),而後獨(dú)言吉兇悔吝生乎動(dòng)者,以動(dòng)詳於變故也。此言吉兇悔吝,而後止言吉兇者,以吉兇者悔吝之積也。
天地之道,貞觀者也;日月之道,貞明者也;天下之動(dòng),貞夫一者也。
【觀,官喚反。夫,音扶】。
○程子曰:天地之道,常垂象以示人,故曰貞觀;日月常明而不息,故曰貞明。
《本義》:觀,示也。天下之動(dòng),其變無(wú)窮,然順理則吉,逆理則兇,則其所正而常者,亦一理而已矣。
○朱子曰:吉兇常相勝,不是吉?jiǎng)賰矗闶莾磩偌叱O鄤伲试回憚佟L斓刂绖t常示,日月之道則常明,天下之動(dòng),貞夫一者也。天下之動(dòng)雖不齊,常有一箇是底,故曰貞夫一。
○雲(yún)峰胡氏曰:上繫於吉兇悔吝無(wú)咎之義,發(fā)之詳矣,獨(dú)貞字未發(fā),故於下繫發(fā)之。貞者,正而固也。《本義》曰:正而常,何哉?固者,人事之當(dāng)然;常者,天理之必然。天下之動(dòng),非吉?jiǎng)賰矗瑒t兇勝吉,二者常相勝而不已,然亦天下之正理也。人之所為,正則吉,不正則兇,雖其動(dòng)也不一,而常有至一者存,亦不外乎此至正之理而已。天地日月之道,亦猶是也。
夫乾確然,示人易矣。夫坤隤然,示人簡(jiǎn)矣。
【確,苦角反。易,以?反。隤,大回反】。
《本義》:確然,健貌。隤然,順貌。所謂貞觀者也。
爻也者,效此者也。象也者,像此者也。
【像音象】。
《本義》: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,爻之奇偶,卦之消息,所以效而象之。
《或問(wèn)》:爻也者,效此者也,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。象也者,像此者也,是象乾坤之虛實(shí)而為奇偶。
○朱子曰:效此便是乾坤之理,象只是像其奇偶。
爻象動(dòng)乎內(nèi),吉兇見(jiàn)乎外,功業(yè)見(jiàn)乎變,聖人之情見(jiàn)乎辭。
【見(jiàn),賢遍反】。
《本義》:內(nèi),謂蓍卦之中。外,謂蓍卦之外。變,即動(dòng)乎內(nèi)之變。辭,即見(jiàn)乎外之辭。
《或問(wèn)》:爻象動(dòng)乎內(nèi),吉兇見(jiàn)乎外,或謂隂陽(yáng)老少,在分蓍揲卦之時(shí),而吉兇乃見(jiàn)於成卦之後,如何?
○朱子曰:也是如此。然內(nèi)外字,猶言先後微顯。
○功業(yè)見(jiàn)乎變,是就那動(dòng)底爻,見(jiàn)得這功業(yè)字,似吉兇生大業(yè)之業(yè),猶言事變庶事相似。
○潘氏曰:確然隤然,乾坤之體也。隤,與頹同。乾坤之所以示人者,易而不難,簡(jiǎn)而不繁。爻者,傚此易簡(jiǎn)者也。象者,像此易簡(jiǎn)者也。及其爻象動(dòng)乎卦之內(nèi),則吉兇見(jiàn)於事之外,功業(yè)見(jiàn)於變通之間。蓋動(dòng)則有吉兇,不動(dòng)則吉兇無(wú)自而生。變則有功業(yè),不變則功業(yè)無(wú)自而成。聖人之情,則見(jiàn)爻辭象辭之間,所以指人以所之也。
天地之大德曰生,聖人之大寶曰位。何以守位?曰仁。何以聚人?曰財(cái)。理財(cái)正辭,禁民為非,曰義。
《本義》曰:人之人,今本作仁,呂氏從古。蓋所謂非衆(zhòng)罔與守邦,
○朱子曰:天地以生物為心,蓋天地之間,品物萬(wàn)形,各有所事。唯天則確然於上,地則隤然於下,一無(wú)所為,只以生物為事。故易曰:天地之大德曰生,聖人之情見(jiàn)乎辭。下連接說(shuō)天地大德曰生,此不是相連,乃各自說(shuō)去。聖人之大寶曰位,有德有位,則事事做得。
○問(wèn):人君臨天下,大小大事,只言理財(cái)正辭,如何?曰:是因上文而言。聚得許多人,無(wú)財(cái)何以養(yǎng)之?有財(cái)不能理,又不得。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。又曰:教化便在正辭裏面。
○理財(cái)、正辭、禁非是三事。大?是辨別是非。理財(cái)言你底還你,我底還我;正辭言是底說(shuō)是,不是底說(shuō)不是,猶所謂正名。
○白雲(yún)郭氏曰:天地以生物為德,故人以大德歸之。聖人得崇高之位,然後成位乎中而贊化育,故以位為大寶也。大寶者,亦非聖人自以為寶也。天下有生,幸聖人之德位以蒙其澤,故天下以為寶也。
○臨川王氏曰:生生不己者,天地之大德。然天地生物生人,又生與天地合德之聖人,命之居君師之位,為人物之主,而後能使天地之所生,得以各遂其生也。茍或但有其德而無(wú)其位,則亦不能相天地而遂人物之生,故位為聖人之大寶。大寶,謂大可貴重。守,謂保有之。必得衆(zhòng)人之歸嚮,乃能保有君師之位。聚,謂養(yǎng)之而使蕃盛衆(zhòng)多也。
○平庵項(xiàng)氏曰:財(cái)者,百物總名,皆民之所利也。正辭,謂殊貴賤使有度,明取予使有義,辨名實(shí)使有信。蓋利之所在,不可不導(dǎo)之使知義也。禁民為非,謂憲禁令,致刑罰,以齊其不可導(dǎo)者也。蓋養(yǎng)之教之而後齊之,聖人不忍之政,盡於此三者矣。理財(cái),則易之備物致用也。正辭,則易之辨物正言也。禁民為非,則易之?dāng)嗉獌矗魇У茫鈨?nèi)使知懼也。易之事業(yè),盡於此三者矣。
○雲(yún)峰胡氏曰:上繫首章,由乾之始,坤之成,說(shuō)歸乾坤易簡(jiǎn)之理。下繫首章,則由乾之易,坤之簡(jiǎn),說(shuō)出天地大生之德。得乾坤易簡(jiǎn)之理,如聖人乃可以成人之位。行天地大生之德,在聖人不可無(wú)大寶之位。兩位字不同。位乎天地之中,人所同也,而聖人能成之。大寶曰位,聖人之所獨(dú)也,而天地實(shí)賴之。上下繫之首章,其有望於後世有德有位之聖人也如此哉!
右第一章
《本義》:此章言卦爻吉兇造化功業(yè)。
雙湖胡氏曰:按此章首論重卦,繫辭有爻象變動(dòng)四者,其下文皆是覆說(shuō)。上面爻畫(huà)剛?cè)嶂儯M辭之動(dòng)兩股,其曰吉兇悔吝生乎動(dòng)者,所以明繫辭焉而命之,動(dòng)在其中之意。其曰剛?cè)崃⒈荆兺ㄚ厱r(shí)者,所以明剛?cè)嵯嗤疲冊(cè)谄渲兄狻6约獌簇憚僖韵拢稚昝骷獌椿诹呱鮿?dòng)一句,謂天地之道以貞而勝,日月之道以貞而明,天下之動(dòng),亦唯當(dāng)一以貞而勝之而已。大抵易為斯人作卦爻辭,無(wú)非所以明失得之報(bào),故說(shuō)吉兇為甚詳也。次論乾坤,易簡(jiǎn)對(duì)天地德生說(shuō),作易聖人以憂世之情,發(fā)明易簡(jiǎn)於卦爻之辭;用易聖人有御世之位,推行德生於仁義之道。前一股是易,後一股是用易。要之,乾坤即天地也,易簡(jiǎn)即大德之生也。作易聖人之情見(jiàn)乎辭,用易聖人以仁守其位,無(wú)非所以為斯人而已耳。合兩節(jié)而觀,一章之旨可見(jiàn)矣。
系辭下傳?第二章
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,仰則觀象於天,俯則觀法於地,觀鳥(niǎo)獸之文與地之宜,近取諸身,遠(yuǎn)取諸物,於是始作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類(lèi)萬(wàn)物之情。
【王于況反】。
○程子曰:近取諸身,一身之上,百理具備,甚物是沒(méi)底?背在上,故為陽(yáng);胷在下,故為隂。至如男女之生,已有此象。天有五行,亦有五藏。心,火也,著些天地間熱氣乘之,則便須發(fā)燥;肝,木也,著些天地風(fēng)氣乘之,則便須怒。推之五藏亦然。
《本義》:王昭素曰:與地之間,諸本多有天字。俯仰遠(yuǎn)近,所取不一,然不過(guò)以驗(yàn)隂陽(yáng)消息兩端而已。神明之德,如健順動(dòng)止之性;萬(wàn)物之情,如雷風(fēng)山澤之象。
○朱子曰:仰則觀象於天一段,只是隂陽(yáng)奇耦。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,都不出隂陽(yáng)兩字。便是河圖、洛書(shū),也只是隂陽(yáng)。
○觀鳥(niǎo)獸之文與地之宜,那時(shí)未有文字,只是仰觀俯察而已。想得聖人心細(xì),雖鳥(niǎo)獸羽毛之微,也盡察得有隂陽(yáng)。今人心麄,如何察得?或曰:伊川見(jiàn)兔曰察,此亦可以畫(huà)卦,便是此義。曰:就這一端上,亦可以見(jiàn)。凡草木禽獸,無(wú)不有隂陽(yáng)。鯉魚(yú)脊上有三十六鱗隂數(shù),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(yáng)數(shù)。龍不曾見(jiàn),鯉魚(yú)必有之。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,兩邊各插四段,共成八段子。八段之外,兩邊周?chē)灿卸亩巍V虚g五段者,五行也;兩邊插八段者,八卦也;周?chē)亩握撸臍庖病9w箇如此。又如草木之有雌雄,銀杏、桐、楮、牝牡麻、竹之類(lèi)皆然。又樹(shù)木向陽(yáng)處則堅(jiān)實(shí),其背隂處必虛軟。男生必伏,女生必偃,其死於水也亦然。蓋男陽(yáng)氣在背,女陽(yáng)氣在腹也。
○以通神明之德,以類(lèi)萬(wàn)物之情,盡于八卦,而震巽坎離艮兌又總於乾坤。曰動(dòng),曰陷,曰止,皆健底意思;曰入,曰麗,曰說(shuō),皆順底意思。聖人下此八字,極狀得八卦性情盡。
○問(wèn):《本義》謂:伏羲作易,驗(yàn)隂陽(yáng)消息兩端而已,此語(yǔ)最盡。曰:隂陽(yáng)雖是兩箇字,然卻是一氣之消息。一進(jìn)一退,一消一長(zhǎng)。進(jìn)處便是陽(yáng),退處便是隂;長(zhǎng)處便是陽(yáng),消處便是隂。只是這一氣之消息,做出古今天地間無(wú)限事來(lái)。所以隂陽(yáng)做一箇說(shuō)亦得,做兩箇說(shuō)亦得。
○柴氏中行曰:仰觀象於天,而參驗(yàn)於鳥(niǎo)獸之文,於是得隂陽(yáng)之理;俯觀法於地,而參驗(yàn)於地宜,於是得剛?cè)嶂椤=≈T身,遠(yuǎn)取諸物,而知理之所在。物我無(wú)二三才之道,默會(huì)於心,要不出乎隂陽(yáng)二端相變而已。
○平庵項(xiàng)氏曰:象以氣言,屬陽(yáng);法以形言,屬隂。鳥(niǎo)獸之文,謂天產(chǎn)之物,飛陽(yáng)而走隂也;土地所宜,謂地產(chǎn)之物,木陽(yáng)而草隂也。
○節(jié)齋蔡氏曰:聖人所畫(huà)之卦,精可以通神明之德,粗可以類(lèi)萬(wàn)物之情。神明之德,不可見(jiàn)者也,故曰通;萬(wàn)物之情,可見(jiàn)者也,故曰類(lèi)。
○雲(yún)峰胡氏曰:神明之德,不外乎健順動(dòng)止八者之德;萬(wàn)物之情,不止乎天地雷風(fēng)八物之情。
作結(jié)繩而為網(wǎng)罟,以佃以漁,蓋取諸離
【罟音古,佃音田】。
○程子曰:聖人制器,不待見(jiàn)卦而後知象,以衆(zhòng)人由之而不能知之,故因卦以示之耳。
《本義》:兩目相承而物麗焉。
○朱子曰:蓋取諸等字,乃模様是恁地,蓋字便是一箇半間半界底字。又曰:據(jù)十三卦取象,蓋取之離者,言繩為網(wǎng)罟,有離之象,非覩離而始有此也。
○誠(chéng)齋楊氏曰:教民肉食,自包犧始。
○南軒張氏曰: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,故伏羲氏為之網(wǎng)罟,以佃以漁,非徒使民皆知鮮食之利,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。取諸離者,蓋離以一隂麗乎二陽(yáng)之間,則鳥(niǎo)獸之麗乎網(wǎng),魚(yú)鼈之麗乎罟,其義可推矣。
○厚齋馮氏曰:離有二義,曰象,曰理。理謂麗也,謂鳥(niǎo)獸魚(yú)鼈麗乎網(wǎng)罟也。象謂虛中,網(wǎng)罟之日虛也。
○雲(yún)峰胡氏曰:民以食為先,自古未有耕種,則鮮食乃其先也。伏羲氏非取諸離然後為網(wǎng)罟,特網(wǎng)罟兩目相承而物麗,自有似於離之象焉耳。蓋之言,疑辭也。下倣此。
包犧氏沒(méi),神農(nóng)氏作,斵木為耜,揉木為耒,耒耨之利,以敎天下,蓋取諸益。
【斵,陟角反。耜,音似。耒,力對(duì)反。耨,奴豆反】。
《本義》:二體皆木,上入下動(dòng),天下之益,莫大於此。
《或問(wèn)》:上入下動(dòng),於取象有所未曉。
○朱子曰:耜乃今之鏵,胡瓜反。鍫,七消反。耒乃鏵柄,雖下入,畢竟是上面用力方得入。
○沙隨程氏曰:飛走之類(lèi),實(shí)害禾稼,唯網(wǎng)罟佃漁之制立,然後耒耨之利見(jiàn)於天下。
○誠(chéng)齋楊氏曰:教民粒食,自神農(nóng)始。
○節(jié)齋蔡氏曰:耜,耒首也,斵木之銳而為之。耒,耜柄也,揉木使曲而為之。
○疉山謝氏曰:耒耜者,今謂之犂。曲木在上,俗名犂衝,即耒也。斵削二片在下,以承鐵二片,俗呼犂壁,即耜也。
○漢上朱氏曰:炎帝時(shí),民厭鮮食,而食草木之實(shí),於是始為耒耜,以教天下,故曰神農(nóng)。耨,耘除草也。
○雲(yún)峰胡氏曰:自古未有牛耕,神農(nóng)教民耒耜。其動(dòng)也,其下之耜;而所以入之者,在上之耒。於益之卦德,上入下動(dòng),蓋有合焉。況為天下之益,於卦名又有合也。
日中為市,致天下之民,聚天下之貨,交易而退,各得其所,蓋取諸噬嗑。
《本義》:日中為市,上明而下動(dòng),又借噬為市,嗑為合也。
○開(kāi)封耿氏曰:有菽粟者,或不足乎禽魚(yú);有禽魚(yú)者,或不足于菽粟。罄者無(wú)所取,積者無(wú)所散,則利市不布,養(yǎng)不均矣。于是日中為市焉。日中者,萬(wàn)物相見(jiàn)之時(shí)也。當(dāng)萬(wàn)物相見(jiàn)之時(shí),而致天下之民,聚天下之貨,使遷其有無(wú),則得其所矣。
○丹陽(yáng)都氏曰:五十里為市,而各致其民,則天下之民無(wú)不致矣。市各聚其貨,則天下之貨無(wú)不聚矣。於是以其所有,易其所無(wú),交易而退,各得其所,則動(dòng)而噬嗑以為養(yǎng),蓋取諸噬嗑也。
○節(jié)齋蔡氏曰:天下之民不同業(yè),天下之貨不同用,致而聚之,噬而嗑之之義。
○進(jìn)齋徐氏曰:噬嗑,離明在上,日中象震動(dòng)於下,致民交易於市之義。
○合沙鄭氏曰:十三卦始離,次益,次噬嗑,所取者食貨而已。食貨者,生民之本也。
神農(nóng)氏沒(méi),黃帝、堯、舜氏作。通其變,使民不倦;神而化之,使民宜之。易:窮則變,變則通,通則久。是以自天祐之,吉無(wú)不利。黃帝、堯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,蓋取諸乾坤。【治,去聲】。
○程子曰:聖人主化,如禹之治水,順則當(dāng)順之,治則順治之。古之伏羲,豈不能垂衣裳?必待堯、舜然後垂衣裳。據(jù)如此事,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,然必須數(shù)世然後成,亦因時(shí)而已。又曰:識(shí)變知化為難。古今風(fēng)氣不同,故器用亦異。是以聖人通變,使民不倦,各隨其時(shí)而已矣。後世雖有作者,虞舜為弗可及矣。蓋當(dāng)是時(shí),風(fēng)氣未開(kāi),而虞舜之德又如此,故後世莫可及也。若三代之治,後世決可復(fù)。不以三代為治者,終茍道也。
《本義》:乾坤變化而無(wú)為,
○朱子曰:黃帝、堯、舜氏作,到這時(shí)候,合當(dāng)如此變。易窮則變,道理亦如此。垂衣裳而天下治,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。通其變,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。若聽(tīng)其自變,如何得?
○南軒張氏曰:作衣裳以被之於身,垂綃為衣,其色元而象道;襞幅為裳,其色纁而象事。法乾坤以示人,使民知君臣、父子、尊卑、貴賤,莫不各安其分也。
○誠(chéng)齋楊氏曰:所謂衣裳,即舜所謂古人之象,五色作服者是也。蓋始於黃帝,備於堯舜。
○疉山謝氏曰:乾,天在上,衣象。衣上闔而圓,有陽(yáng)奇象。坤,地在下,裳象。裳下兩股,有隂偶象。上衣下裳,不可顛倒,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亂,則民志定,天下治矣。
○建安丘氏曰:十三卦制器而尚象,皆通變宜民之事。特於黃帝、堯、舜氏言之者,犧農(nóng)之時(shí),人害雖消,而人文未著;衣食雖足,而禮義未興。為之君者,方且與民竝耕而食,饔飱而治,蚩蚩蠢蠢,蓋未識(shí)所謂上下尊卑之分。於是三聖人者,仰觀俯察,體乾坤之象,正衣裳之儀,使君臣分義,截然於天高地下之間,天下其有不治乎?斯時(shí)也,其世道一新之會(huì),而黎民於變之機(jī)也。
○雲(yún)峰胡氏曰:食貨既足,不可無(wú)禮,於是垂衣裳以明尊卑貴賤之分,而於乾坤之尊卑有合。然垂衣裳而天下治,即乾坤之變化而無(wú)為也。
刳木為舟,剡木為楫,舟楫之利,以濟(jì)不通,致遠(yuǎn)以利天下,蓋取諸渙。
【刳,口姑反。剡,以冉反】。
《本義》:木在水上也。致遠(yuǎn)以利天下,疑衍。
○南軒張氏曰:衣裳之垂□,欲遠(yuǎn)近之民,下觀而化。然川途之險(xiǎn)阻,則有所不通。唯夫舟楫之利既興,則日月所照,霜露所墜,莫不拭目觀化,天下如一家,中國(guó)如一人矣。是以刳其木而中虛,剡其楫而末銳。舟所以載物,而楫所以進(jìn)舟。致遠(yuǎn)以利天下,而取諸渙者,蓋渙之成卦,上巽下坎。彖曰:利涉大川,乘木有功也。
服牛乘馬,引重致遠(yuǎn),以利天下,蓋取諸隨。
○程子曰:服牛乘馬,皆因其性而為之,胡不乘牛而服馬乎?理之所不可也。
《本義》下動(dòng)上說(shuō)。
漢上朱氏曰:上古牛未穿,馬未絡(luò),至是始服乘之。
○鄱陽(yáng)董氏曰:服牛乘馬,穿鼻絡(luò)頭,雖人為也,亦各因其天而任之,故取諸隨。
○安定胡氏曰:隨者,是動(dòng)作必隨於人,以之遠(yuǎn)則隨於人,以之近則亦隨於人。
○李氏曰:刳木為舟,剡木為楫,因植物之材而川通矣。服牛乘馬,引重致遠(yuǎn),因動(dòng)物之性而途通矣。牛以順為道,故服而馴之以引重;馬以行為事,故乘而駕之以致遠(yuǎn)。牛非不可以致遠(yuǎn),於引重為力而已;馬非不可以引重,於致遠(yuǎn)為敏而已。引重謂之引,以有所進(jìn)為義;致遠(yuǎn)謂之致,以有所至為義。
重門(mén)擊柝,以待暴客,蓋取諸豫
【重,直龍反。柝,他洛反】。
《本義》:豫備之意。
○朱子曰:重門(mén)擊柝,以待暴客,只是豫備之意,卻須待用互體推艮為門(mén)闕,雷震乎外之義。剡木為矢,弦木為弧,只是睽乖,故有威天下之象。亦必待穿鑿附會(huì),就卦推出制器之義,殊不知卦中但有此理而已。故孔子各以蓋取諸某卦言之,亦曰其大意云爾。漢書(shū)所謂獲一角獸,蓋麟云,皆疑辭也。
○漢上朱氏曰:上古外戶不閉,禦風(fēng)氣而已,至是始有暴客之防。
○楊氏曰:川途既通,則暴客至矣。又不可無(wú)禦之之術(shù),故取諸豫。重門(mén)以禦之,擊柝以警之,則暴客無(wú)自而至。二隂在前,重門(mén)之象也。一陽(yáng)在下,擊柝之象也。三隂安於內(nèi),說(shuō)豫之象也。
○涑水司馬氏曰:豫者,怠惰之意。擊柝者,所以警怠惰也。
斷木為杵,掘地為臼,臼杵之利,萬(wàn)民以濟(jì),蓋取諸小過(guò)。
【斷,丁緩反。杵,昌呂反。掘,其曰反】。
《本義》:下止上動(dòng),
○誠(chéng)齋楊氏曰:耒耜,耕稼之始。臼杵,脫粟之始。
○建安丘氏曰:以象言之,上震為木,下艮為土,震木上動(dòng),艮土下止。杵臼,治米之象。
○進(jìn)齋徐氏曰:民粒食矣,又杵臼以治之,而使精小有所過(guò)而利人者也。
弦木為弧,剡木為矢,弧矢之利以威天下,蓋取諸睽。
《本義》:睽乖然後威以服之。
○南軒張氏曰:外有擊柝以防暴客,內(nèi)有杵臼以治粒食,而無(wú)以威其不軌,則雖有險(xiǎn)不能守,雖有粟而不得食,此弧矢之利不可緩也。
○臨川吳氏曰:弧,木弓也。兵器不一,弓矢所及者遠(yuǎn),為長(zhǎng)兵威天下者,示有警備而使之畏也。
○漢上朱氏曰:知門(mén)柝而不知弧矢之利,則威天下者有未盡,故教之以弧矢之利。
○進(jìn)齋徐氏曰:其害之大者,以重門(mén)擊柝不足以待之,故必有弧矢以威之。利天下者,仁也;威天下者,義也。
上古穴居而野處,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,上棟下宇,以待風(fēng)雨,蓋取諸大壯。
○程子曰:上古之時(shí),民皆巢居而穴處。後世易之以棟宇,而不以巢居穴處為可變者,以棟宇之利故也】。《本義》壯固之意。
○節(jié)齋蔡氏曰:棟,屋脊檁也。宇,椽也。棟直承而上,故曰上棟;宇兩垂而下,故曰下宇。棟取四剛義,宇取二柔義。
○涑水司馬氏曰:風(fēng)雨,動(dòng)物也。風(fēng)雨動(dòng)於上,棟宇建於下,大壯之象也。
○進(jìn)齋徐氏曰:冬穴居無(wú)以待風(fēng),夏野處無(wú)以待雨,故宮室不得不興。震風(fēng)凌雨,然後知廈屋之為帡幪,故棟宇不可不固,大壯之意也。
古之葬者,厚衣之以薪,葬之中野,不封不樹(shù),喪期無(wú)數(shù)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,蓋取諸大過(guò)。
【衣於既反】。
《本義》:送死大事而過(guò)於厚。
○南軒張氏曰: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,於此而過(guò)無(wú)害也。
○丹陽(yáng)都氏曰:杵臼棺槨,所以使民養(yǎng)生送死無(wú)憾,所以依於人者過(guò)厚也。然養(yǎng)生不足以當(dāng)大事,故取小過(guò)之義而已;送死足以當(dāng)大事,故取大過(guò)之義焉。
○合沙鄭氏曰:大壯外震,震,動(dòng)也,風(fēng)雨飄搖之象。大過(guò)內(nèi)巽,巽,入也,殯葬入土之象。
上古結(jié)繩而治,後世聖人易之以書(shū)契,百官以治,萬(wàn)民以察,蓋取諸夬。
《本義》:明決之意。
○朱子曰:上古結(jié)繩而治,後世聖人易之以書(shū)契。天下事有古木之為,而後人為之,固不可無(wú)者,此類(lèi)是也。又曰:結(jié)?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。又有刻版者,凡年月日時(shí),以至人馬糧草之?dāng)?shù),皆刻版為記,都不相亂。
○問(wèn):六十四卦重於伏羲,果否?曰:此不可考。或曰:耒耜市井已取重卦之象,則疑伏羲已重卦。或者又謂此十三卦皆云蓋取,則亦疑辭,未必因見(jiàn)此卦而制此物也。今無(wú)所考,但既有八卦,則六十四卦已在其中,此則不可不知耳。
○進(jìn)齋徐氏曰:上古民淳事簡(jiǎn),事之小大,唯結(jié)?以識(shí)之,亦足以為治。至後世風(fēng)俗媮薄,欺詐日生,而書(shū)契不容不作矣。書(shū),文字也。契,合約也。言有不能記者,書(shū)識(shí)之;事有不能信者,契驗(yàn)之,取明決之義。蓋夬乃君子決小人之卦,而造書(shū)契者,亦所以決去小人之偽,而防其欺也。
○開(kāi)封耿氏曰:已前不云上古,已下三事,或言古與上不同者,蓋未造此器之前,更無(wú)餘物之用,非是後世以替前物,故不言上古也。此以下三事,皆是未造此物之前,已更別有所用,今將後用而代前用,故本之云上古及古者。
右第二章
《本義》: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。
○息齋余氏曰:卜筮之說(shuō)詳於上繫,制器之說(shuō)詳於下繫。
○潛室陳氏曰:十三卦取象說(shuō),上古雖未有易之書(shū),元自有易之理,故所作事暗合易書(shū),即邵子所謂畫(huà)前之易是也。
○開(kāi)封耿氏曰:十三卦之辭,或言利,或不言利,何也?網(wǎng)罟非不為利也,然必耒耜、杵臼而後能裕萬(wàn)民之食,是則網(wǎng)罟之利不足言,而耒耜、杵臼之利大矣,所以言利也。門(mén)柝非不為利也,然門(mén)柝則能保其內(nèi),使暴客不能入而已。弧矢則又能威其外,使暴客不能至,是則門(mén)柝之利不足言,而弧矢之利大矣,所以言利也。獨(dú)於舟楫、馬牛言利天下者,舟楫、馬牛之利無(wú)所不通,可以周天下故也。
○茍軒程氏曰:網(wǎng)罟、耒耜所以足民食,交易、舟車(chē)所以通民財(cái),杵臼、弧矢所以利民用。衣裳以華其身,宮室以定其居,門(mén)柝以衛(wèi)其生,棺槨以送其死,凡所以為民生利用、安身、養(yǎng)生、送死之道,已無(wú)遺憾矣。然百官以治,萬(wàn)民以察,卒歸之夬之書(shū)契,何也?蓋器利用便,則巧偽生,憂患作,聖人憂之,故終之以書(shū)契之取象。書(shū)契可以代忘言之兌,乾天可以防書(shū)契之偽,其視網(wǎng)罟等象,雖非一時(shí)之利,實(shí)萬(wàn)世之大利也。故結(jié)?初易為網(wǎng)罟,終易為書(shū)契。聖人以定大業(yè),斷大疑,悉於書(shū)契乎?觀百官,治萬(wàn)民,察誠(chéng)非書(shū)契不可也。十三卦終以夬卦之取象,聖人之意深矣。
○雲(yún)峰胡氏曰:舟楫取渙,以卦象取也。服乘取隨,臼杵取過(guò),以卦德取也。豫備睽乖,壯固夬決,大過(guò)過(guò)於厚,皆以卦義取也。諸家往往皆以互體推之,未免穿鑿。殊不知夫子之意,亦不過(guò)謂聖人之制此器也,此卦之中自有此理而已。蓋之一字,疑取諸此,而非必取之此也。自天祐之,吉無(wú)不利,上傳為君子之用易者言之,下傳又為聖人之通變者言之,何也?天者,理而已。聖人之制器,不能先天而強(qiáng)為,不能後天而不為,非一時(shí)之所可為也,非一人之所能為也,皆天理之自然者也,所以亦曰自天祐之。
○誠(chéng)齋楊氏曰:嗚呼!鴻荒之世,民之初生,非若今日之備器用,便起居。其服食也,自斯人之飢而未知佃漁也,聖人於是乎作網(wǎng)罟。自斯人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,聖人於是乎作耒耜。自斯人之食貨或有餘或不足之偏匱也,聖人於是乎作市易。自斯人之寒而衣皮未知織紝之制也,聖人於是乎作衣裳。自斯人之出入厄於川隔而道斷也,聖人於是乎作舟楫;自斯人之疲於負(fù)擔(dān),而趼於遠(yuǎn)塗也,聖人於是乎作輪轡;自斯人之虞於寇攘,而懈於守禦也,聖人於是乎作門(mén)柝;自斯人之知有耕耨,而未知有春揄也,聖人於是乎作杵臼;自斯人之無(wú)爪牙以自濟(jì),而憂於搏噬也,聖人於是乎作弧矢;自斯人之穴處,而病於溼墊也,聖人於是乎作宮室;自斯人之死,而蹙於虆梩之掩也,聖人於是乎作棺槨;自斯人之窮於結(jié)繩,而相欺無(wú)藉也,聖人於是乎作書(shū)契。然非聖人之私知也,取於十三卦之象然後成;亦非一聖人之能為也,歷五聖人而後備。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,而聖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。故曰:如古之無(wú)聖人,人之類(lèi)滅久矣。
○西山真氏曰:此章所列卦象之意,皆物理之自然者也。有自然之象,則有自然之理,人之所共睹也。然常人見(jiàn)其象而昧其理,唯聖人見(jiàn)是象則知是理,知是理則制是器。人皆謂備物致用,立成器以利天下,出於聖人之心思,不知聖人亦因其所固有而已。學(xué)者誠(chéng)能虛心以體天下之物,則精義妙道,莫不昭昭然接於吾之心日,然後真知道器之相合,而顯微之無(wú)間也。
系辭下傳?第三章
是故易者,象也;象也者,像也。
《本義》:易,卦之形,理之似也。
○朱子曰:易者象也,象也者像也,只是彷彿說(shuō),不可求得太深。
○易者象也,是總說(shuō)起,言易不過(guò)只言隂陽(yáng)之象。下云像也,材也,天下之動(dòng)也,則皆是說(shuō)那上面象字。
○問(wèn):易者象也,象也者像也四句,莫只是解箇象字否?曰:是解易字,像又是解象字,材又是解彖字。末句意亦然。
○蔡氏攸曰:昔者聖人之作易也,始畫(huà)八卦,而象在其中。象與卦竝生,以寓天下之賾,故曰易者象也。蓋俯仰以觀,遠(yuǎn)近以取,神明之德可通,鬼神之情狀可得,而況於人乎?況於萬(wàn)物乎?及因而重之,發(fā)揮於剛?cè)岫常瑒t擬諸其形容者,其變不一,而象亦為之滋矣。故邑屋、宮庭、舟車(chē)、器械、服帶、簪履,下至鳥(niǎo)獸、蟲(chóng)魚(yú)、金石、草木之類(lèi),皆在所擬,至纖至悉,無(wú)所不有。所謂其道甚大,百物不廢者,此也。其在上古,尚此以制器;其在中古,觀此以繫辭。而後世之言易者,乃曰得意在忘象,得象在忘言,一切指為魚(yú)兔筌蹄,殆非聖人作易,前民用以教天下之意也。
彖者,材也。
《本義》:彖言一卦之材。
漢上朱氏曰:卦有剛?cè)幔囊病S惺菚r(shí),有是象,必有是才以濟(jì)之。才與時(shí)會(huì),斯足以成務(wù)矣。
爻也者,效天下之動(dòng)者也。
《本義》:效,放也。
漢上朱氏曰:天下之動(dòng),其微難知,有同處一時(shí),同處一事,所當(dāng)之位,有不同焉,則進(jìn)退趨舍殊塗矣,故曰爻也者,效天下之動(dòng)也。
是故吉兇生而悔吝著也。
《本義》:悔吝本微,因此而著。
○南軒張氏曰:易者,象也。象也者,像此者也。謂之彖,則言其象之材而已。謂之爻,則放其象之變而已。至於吉兇,則悔吝之著也。故悔者有改過(guò)之意,而吉?jiǎng)t悔之著也。吝者有文過(guò)之意,而兇則吝之著也。
○雲(yún)峰胡氏曰:至著者象,至微者理。易之象,理之似也。彖者,材也。材者,象之質(zhì)。爻效天下之動(dòng),動(dòng)者,象之變。悔吝在心未著,吉兇在事已著。吉者悔之著,兇者吝之著也。
右第三章。
雙湖胡氏曰:此章說(shuō)卦象及彖辭爻辭,論人事之悔吝,至吉兇而始著。蓋卦爻辭無(wú)非所以明得失之報(bào),欲人觀象玩辭之際,知有悔心而不吝於改過(guò),庶幾有吉而無(wú)兇耳。
系辭下傳?第四章
陽(yáng)卦多隂,隂卦多陽(yáng)。
《本義》:震、坎、艮為陽(yáng)卦,皆一陽(yáng)二隂。巽、離、兌為隂卦,皆一隂二陽(yáng)。
潛室陳氏曰:二耦一奇,即奇為主,是為陽(yáng)卦。二奇一耦,即耦為主,是為隂卦。故曰陽(yáng)卦多隂,隂卦多陽(yáng)。
其故何也?陽(yáng)卦奇,隂卦耦。
《本義》:凡陽(yáng)卦皆五畫(huà),凡隂卦皆四畫(huà)。
○二山林氏曰:陽(yáng)卦宜多陽(yáng)而多隂,隂卦宜多隂而多陽(yáng),何也?蓋陽(yáng)卦之?dāng)?shù)必五,奇數(shù)也,奇則隂畫(huà)自多。隂卦之?dāng)?shù)必四,耦數(shù)也,耦則陽(yáng)畫(huà)自多。其多隂多陽(yáng)皆自然而然,非人力所能參也。
○雙湖胡氏曰:嘗推八卦奇耦之畫(huà),每卦雖各得其三,而合之則為六。乾坤合為六,震巽合亦六,坎離合亦六,艮兌合亦六,適符老隂掛扐之用數(shù)。總之則四六二十四畫(huà),而成老隂過(guò)揲之?dāng)?shù),若無(wú)與於老陽(yáng)之?dāng)?shù)矣。然以陽(yáng)卦五畫(huà)、隂卦四畫(huà)觀之,奇耦之合又皆老陽(yáng)掛扐之用數(shù),故乾坤合為九,震巽合亦九,坎離合亦九,艮兌合亦九,悉數(shù)之實(shí)成三十六,而為老陽(yáng)過(guò)揲之?dāng)?shù)焉。此乾坤用九用六,其數(shù)默見(jiàn)於卦畫(huà)之可推者如此。雖出於偶然,其實(shí)亦莫非自然之妙也,豈可以人力參哉?
其德行何也?陽(yáng)一君而二民,君子之道也;隂二君而一民,小人之道也。
【行,下孟反】。
《本義》:君謂陽(yáng),民謂隂。
○朱子曰:二君一民,試敎一箇民而有兩箇君,看是甚模様。
○柴氏中行曰:一君二民,道大而公,君子之道也。二君一民,道小而私,小人之道也。卦體乎君子小人之道,而象彖爻所以發(fā)明此道者也。然在諸卦,為陽(yáng)卦者,未必皆君子之道。為隂卦者,未必皆小人之道。蓋此特借隂陽(yáng)二卦之體,以明君子小人之道不同耳,非可一例成卦也。爻彖象乃是發(fā)明此道,非發(fā)明此卦也。
○雲(yún)峰胡氏曰:論其故,則陽(yáng)卦五畫(huà),隂卦四畫(huà),陽(yáng)與隂一定之分固如此。論其德行,則陽(yáng)為君,隂為民,陽(yáng)為君子,隂為小人,易之扶陽(yáng)抑隂又如此。
右第四章。
雙湖胡氏曰:此章專(zhuān)以八卦隂陽(yáng)畫(huà)數(shù),分君子小人之道。
系辭下傳?第五章
易曰:憧憧往來(lái),朋從爾思。子曰:天下何思何慮?天下同歸而殊塗,一致而百慮,天下何思何慮?
【憧音沖。
《本義》:此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,言理本無(wú)二,而殊塗百慮,莫非自然,何以思慮為哉?必思而從,則所從者亦狹矣。
○朱子曰:所謂天下何思何慮,正謂雖萬(wàn)變之紛紜,而所以應(yīng)之各有定理,不假思慮而知也。問(wèn):天下同歸而殊塗,一致而百慮,何故不云殊塗而同歸,百慮而一致?曰:也只一般,但他是從上說(shuō),下自合如此說(shuō)。感應(yīng)之理,本不消思慮,空費(fèi)思量,空費(fèi)計(jì)較,空費(fèi)安排,只順其自然而已。
○臨川吳氏曰:思者,心之用也。慮者,謀度其事也。心體虛雲(yún),如止水明鏡,未與物接,寂然不動(dòng),何思之有?既與物接,應(yīng)之各有定理,何慮之有?理之在心者同,因事之不同,而所行之塗各殊。理之在心者一,因事之不一,而所發(fā)之慮有百。塗雖殊,慮雖百,而應(yīng)事之理則同而一也。故定心應(yīng)事,動(dòng)而無(wú)動(dòng),則亦何思何慮之有?此人心定應(yīng)寂然之感也。若九四之憧憧,則豈如是乎?
○柴氏中行曰:言天地萬(wàn)物皆本於天理之自然,人當(dāng)棄私欲而循天理也。所謂理,夫子之一貫,子思之誠(chéng),曾子之守約是也。同歸而殊塗,天下無(wú)二理也。一致而百慮,天下無(wú)二心也。致,謂極致。明其所同歸,極其所一致,則天下雖塗殊慮百,無(wú)不應(yīng)者,何以思慮為哉?
○進(jìn)齋徐氏曰:塗雖殊而歸同,則往來(lái)自不容無(wú),而加之憧憧則私矣。慮雖百而致一,則思亦人心所當(dāng)有,而局於朋從則狹矣。人於此但當(dāng)以貞守之,不必自為紛紛也。
日往則月來(lái),月往則日來(lái),日月相推而明生焉。寒往則暑來(lái),暑往則寒來(lái),寒暑相推而歲成焉。往者屈也,來(lái)者信也,屈信相感而利生焉。
【信音申】。
《本義》:言往來(lái)屈信,皆感應(yīng)自然之常理,加憧憧焉,則入於私矣,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。
○朱子曰:日往則月來(lái)一段,乃承上文憧憧往來(lái)而言。往來(lái)皆人所不能無(wú)者,但憧憧則不可。
○誠(chéng)齋楊氏曰:觀諸日,今夕之往,所以為來(lái)朝之來(lái)。觀諸月,今夕之來(lái),所以為來(lái)朝之往。蓋前之屈,乃後之信也。觀諸寒暑,折膠之寒,不生於寒,而生於烈日流金之暑。流金之暑,不生於暑,而生於堅(jiān)氷折膠之寒。蓋今之信,乃昔之屈也。
○臨川吳氏曰:因日之往,而有月之來(lái)。因月之往,而有日之來(lái)。二曜相推以相繼,則明生而不匱。因寒之往,而有暑之來(lái)。因暑之往,而有寒之來(lái)。二氣相推以相代,則歲成而不缺。往者之屈,感來(lái)者之信。來(lái)者之信,又感往者之屈,而有明生歲成之利。此天道往來(lái)自然之感也。若九四之往來(lái),則豈如是乎?
○張子曰:屈信相感,而利生焉,感以誠(chéng)也。情偽相感,而利害生,雜以偽也。
尺蠖之屈,以求信也。龍蛇之蟄,以存身也。精義入神,以致用也。利用安身,以崇德也。
【蠖,紀(jì)縛反】。
《本義》因言屈信往來(lái)之理,而又推以言學(xué),亦有自然之機(jī)也。精研其義,至於入神,屈之至也,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。利其施用,無(wú)適不安,信之極也,然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。內(nèi)外交相養(yǎng),互相發(fā)也。
○朱子曰:尺蠖之屈,以求信也;龍蛇之蟄,以存身也。屈信消長(zhǎng),闔闢往來(lái),其機(jī)不曾停息。大處有大闔闢,小處有小闔闢;大處有大消息,小處有小消息。此理萬(wàn)古不易。如目有瞬時(shí),亦豈能常瞬,定又須開(kāi);不能常開(kāi),定又須瞬。瞬了又開(kāi),開(kāi)了又瞬,至纎至微,無(wú)時(shí)不然。
○問(wèn):此章言萬(wàn)變雖不同,然皆一理之中所自有知,不用安排。曰:此只說(shuō)得一頭。尺蠖若不屈,則不信得身;龍蛇若不蟄,則不伏得氣,如何存得身?精義入神,疑與行處不相關(guān),然而見(jiàn)得道理通徹,乃所以致用。利用安身,亦疑與崇德不相關(guān),然而動(dòng)作得其理,則德自崇。天下萬(wàn)事萬(wàn)變,無(wú)不有感通往來(lái)之理。又曰:尺蠖屈,便要求信;龍蛇蟄,便要存身。精研義理,無(wú)絲毫之差,入那神妙處,這便是要出來(lái)致用。外面用得利而身安,乃所以入來(lái)自崇已德。致用之用,即利用之用,所以橫渠云:精義入神,事豫吾內(nèi),求利吾外;利用安身,素利吾外,致養(yǎng)吾內(nèi)。事豫吾內(nèi),言曾到這裏面來(lái)。又曰:尺蠖屈得一寸,便能信得一寸來(lái)許,他之屈,乃所以為信。龍蛇於冬若不蟄,則凍殺了,其蟄也,乃所以存身也。精義入神,乃所以致用也;利用安身,乃所以崇德也。欲罷不能,如人行步,左腳起了,不由得右腳不起,所謂過(guò)此以往,未之或知也。若到那窮神知化,則須是德之盛也,方能
○精義二字。所謂義者,宜而已。物之有宜有不宜,事之有可有不可,吾心處之,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,所謂義也。精義者,精諸此而已。所謂精云者,猶曰察之云耳。精之至而入於神,則於事物之所宜,毫釐委曲之間,無(wú)所不悉,有不容言之妙矣。此所以致用,而用無(wú)不利也。又曰:義至於精,則應(yīng)事接物間,無(wú)一非義,不問(wèn)小事大事,千變?nèi)f化,改頭換面出來(lái),自家應(yīng)付他,如利刀快劒相似,迎刃而解,件件判作兩邊去。
○且如精義入神,如何不思那致用底,卻不必思致用底是事功,是效驗(yàn)。
○利用安身,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,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。
○息齋余氏曰:既曰屈信相感,而利生矣。恐人知信之利,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,故以尺蠖、龍蛇明之,其為人切矣。
○臨川吳氏曰:夫子既以屈信二字釋往來(lái)之相感,復(fù)以物理之屈信、聖學(xué)之屈信言之,而廣其意。尺蠖不屈,則其行不能信,既信而再行,則又屈也。龍蛇不蟄,則其來(lái)歲之身不能奮,既奮於來(lái)歲,則又蟄也。此物理之屈信相感也。義理精明,則應(yīng)物有定,而神不外馳,入者無(wú)出,內(nèi)之屈也,而乃所以致極其外之用,屈之感信也。日用宜利,則每事曲當(dāng),而身之所處,隨寓而安,外之信也,而乃所以增崇其內(nèi)之德,信之感屈也。此聖學(xué)之屈信相感也。因言聖學(xué)之交相養(yǎng),互相發(fā),工力至此,則蔑以加矣。
過(guò)此以往,未之或知也。窮神知化,德之盛也。
《本義》下學(xué)之事,盡力於精義利用,而交養(yǎng)互發(fā)之機(jī)自不能己。自是以上,則亦無(wú)所用其力矣。至於窮神知化,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。然不知者往而屈也,自致者來(lái)而信也,是亦感應(yīng)自然之理而已。
○張子曰:氣有隂陽(yáng),推行有漸為化,合一不測(cè)為神。此上四節(jié)皆以釋咸九四爻義。
○朱子曰:窮神知化,德之盛。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,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,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,自誠(chéng)而明相似。又曰:精義入神,以致用也。利用安身,以崇德也。過(guò)此以往,未之或知也。窮神知化,德之盛也。只是這一箇,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。做來(lái)做去,做到徹處便是。
○木之或知,是到這裏不可奈何。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出來(lái),然也有這箇意思。
○神化二字,雖程子說(shuō)得亦不甚分明,唯是橫渠推出來(lái)。推行有漸為化,合一不測(cè)為神。又曰:一故神,兩在故不測(cè),兩故化。
○窮神知化,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,一日復(fù)一日,一月復(fù)一月,節(jié)節(jié)挨將去,便成一年。神是一箇物事,或在彼,或在此,當(dāng)其在隂時(shí)全體在隂,在陽(yáng)時(shí)全體在陽(yáng),都只是這一物,兩處都在,不可測(cè),故謂神。橫渠言:一故神,兩故化。又注云:兩在故不測(cè)。這說(shuō)得甚分曉。
○此章解咸九四。據(jù)爻義看,上文說(shuō)貞吉悔亡,貞字甚重。程子謂:聖人感天下如兩暘,寒暑無(wú)不通,無(wú)不應(yīng)者,貞而已。所以感人者果貞矣,則吉而悔亡。蓋天下本無(wú)二理,果同歸矣,何患乎殊塗?果一致矣,何患乎百慮?所以重言何思何慮也。如日月寒暑之往來(lái),皆是自然感應(yīng)如此。日不往則月不來(lái),月不往則日不來(lái),寒暑亦然。往來(lái)只是一般往來(lái),但憧憧之往來(lái)者,患得患失。既要感這箇,又要感那箇,便自憧憧忙亂,用其私心而已。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者,有晝必有夜。設(shè)使長(zhǎng)長(zhǎng)為晝而不夜,則何以息?夜而不晝,焉得有此光明?春氣同是和好,只有春夏而無(wú)秋冬,萬(wàn)物何以成?一向秋冬而無(wú)春夏,人何以生?屈信往來(lái)之理,所以必待迭相為用,而使利所由生。春秋冬夏,只是一箇感應(yīng),所應(yīng)復(fù)為感,所感復(fù)為應(yīng)也。春夏是一箇大感,秋冬則必應(yīng)之,而秋冬又為春夏之感。以細(xì)言之,則春為夏之感,夏則應(yīng)春而又為秋之感;秋為冬之感,冬則應(yīng)秋而又為春之感,所以不窮也。尺蠖不屈,則不可以信;龍蛇不蟄,則不可以藏身。今山林冬暖,而蛇出者往往多死,此則屈信往來(lái),感應(yīng)必然之理。夫子因往來(lái)兩字說(shuō)得許多大,又推以言學(xué)所以內(nèi)外交相養(yǎng),亦只是此理而已。橫渠曰:事豫吾內(nèi),求利吾外;素利吾外,致養(yǎng)吾內(nèi)。此下學(xué)所當(dāng)致力處。過(guò)此以上,則不容訃。較所謂窮神知化,乃養(yǎng)盛自致,非思勉所及,此則聖人事矣。
○天下何思何慮一段,此是言自然而然。如精義入神,自然致用;利用安身,自然崇德。
○天下何思何慮一句,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,卻說(shuō)同歸殊塗,一致百慮,又再說(shuō)天下何思何慮,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(lái),而如此朋從之思也。日月寒暑之往來(lái),尺蠖龍蛇之屈信,皆是自然底道理。不往則不來(lái),不屈則亦不能信也。今之為學(xué),亦只是如此。精義入神,用力於內(nèi),乃所以致用乎外;利用安身,求利於外,乃所以崇德乎內(nèi)。只是如此做將去,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,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,何思何慮之有?
○雲(yún)峰胡氏曰:天下何思何慮一語(yǔ),所以破思慮之感,息憧憧之思也。天下間凡一往一來(lái),皆感應(yīng)自然之常理,非唯日月寒暑如此。以吾之學(xué)言之,精義以致用,利用以崇德,亦有自然屈信之理。至於窮神知化,而德之盛皆自然而已矣,皆非思慮所及,故曰天下何思何慮。
易曰:困于石,據(jù)于蒺藜,入于其宮,不見(jiàn)其妻,兇。子曰:非所困而困焉,名必辱;非所據(jù)而據(jù)焉,身必危。既辱且危,死期將至,妻其可得見(jiàn)邪?
《本義》:釋困六三爻義。
《或問(wèn)》:非所困而困焉,名必辱,大意謂石不能動(dòng)底物,自是不須去動(dòng)他,若只管去用力,徒自困耳。
○朱子曰:此爻大意謂不可做底,便不可入頭去做。又曰:且以人事言之,有著力不得處,若只管著力去做,少間去做不成,他人便道自家無(wú)能,便是辱了。名
○南軒張氏曰:有應(yīng)於上,將以求名,今用於石,此非所困而困焉,名必辱也。有依於下,得以安身,今據(jù)于蒺藜,非所據(jù)而據(jù)焉,身必危也。在用之時(shí),名辱身危,有死之理,此身不行道,雖妻且不可見(jiàn),宜乎兇也。
○誠(chéng)齋楊氏曰:君子有不幸之困,無(wú)以致之,在陳畏匡是已,故名不辱而身不危。小人無(wú)幸免之困,為不善以致之,以其非所據(jù)而據(jù),是以非所困而困,尚可得而保其名、保其身、保其家、保其妻子乎?
易曰: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,獲之,無(wú)不利。子曰:隼者,禽也;弓矢者,器也;射之者,人也。君子藏器於身,待時(shí)而動(dòng),何不利之有?動(dòng)而不括,是以出而有獲。語(yǔ)成器而動(dòng)者也。
【射,食亦反。隼,恤允反。括,古活反】。
《本義》:括,結(jié)礙也。此釋解上六爻義。
○朱子曰:張敬夫說(shuō)易,謂只依孔子繫辭說(shuō)便了。如說(shuō)公用射隼至成器而動(dòng)者,也只如此說(shuō)便了。固是如此,聖人之意只恁地說(shuō)不得。緣在當(dāng)時(shí)只理會(huì)得象數(shù),故聖人明之以理。又曰:公用射隼,孔子是發(fā)出言外之意。
○漢上朱氏曰:藏可用之器,待可為之時(shí),動(dòng)無(wú)結(jié)礙,出則有獲。唯乘屈信之理,而其用利者能之。
子曰:小人不恥不仁,不畏不義,不見(jiàn)利不勸,不威不懲。小懲而大誡,此小人之福也。易曰:屨校滅趾,無(wú)咎。此之謂也。
《本義》:此釋噬嗑初九爻義。
○厚齋馮氏曰:不以不仁為恥,故見(jiàn)利而後勸於為仁;不以不義為畏,故畏威而後懲於不義。
○漢上朱氏曰:小人不恥不仁,故不畏不義。陷於死亡,辱及其先,恥孰大焉。雖愚也,而就利避害與人同,故見(jiàn)利而後勸,威之而後懲。小懲大誡,猶為小人之福,況真知義乎!
善不積不足以成名,惡不積不足以滅身。小人以小善為無(wú)益而弗為也,以小惡為無(wú)傷而弗去也,故惡積而不可掩,罪大而不可解。易曰:何校滅耳,兇。
【何,河可反。去,羌呂反】。
《本義》:此釋噬嗑上九爻義。
漢上朱氏曰:精於義者,豈一日積哉。彼積不善而滅其身者,不知小善者,大善之積也。
○融堂錢(qián)氏曰:積字宜玩,凡善惡未有不由積而成也。
○誠(chéng)齋楊氏曰:夫子釋噬嗑初上之辭,謂懲惡在初,改過(guò)在小。
○建安丘氏曰:惡小而不能懲,則罪大而不可解,猶滅趾不防而至於滅耳也,烏得而不兇。
子曰:危者,安其位者也;亡者,保其存者也;亂者,有其治者也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,存而不忘亡,治而不忘亂,是以身安而國(guó)家可保也。易曰:其亡其亡,繫于苞桑。
《本義》此釋否九五爻義。
《或問(wèn)》:危者以其位為可安,而不知戒懼,故危。亡者以其存為可常保,是以亡。亂者有其治,是自有其治,如有其善之有,是以亂。
○朱子曰:某舊也如此說(shuō),看來(lái)保字說(shuō)得較牽強(qiáng)。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意,則可以安其位,保其存,有其治。
○臨川吳氏曰:自處?kù)段U撸俗园财湮恢酪病C乎若將亡將亂者,乃所以常保其存,常有其治也。九五否將休矣,而不忘戒懼如此。蓋於安存治之時(shí),而能不忘危亡亂之禍,是以身之位得以安,而國(guó)家可保其久存長(zhǎng)治也。
○張子曰:明君子之見(jiàn)幾。
子曰:德薄而位尊,知小而謀大,力小而任重,鮮不及矣。易曰:鼎折足,覆公餗,其形渥,兇。言不勝其任也。
【知,音智。鮮,仙善反。折,之設(shè)反。餗,音速。渥,於角反。勝,音升】。
《本義》:此釋鼎九四爻義。
漢上朱氏曰:位欲當(dāng)?shù)拢\欲量知,任欲稱(chēng)力,三者各得其實(shí),則利用而安身。小人志在於得而已,以人之團(tuán),徼倖萬(wàn)一,鮮不及禍。自古一敗塗地,殺身不足以塞其責(zé)者,本於不知義而已。
○融堂錢(qián)氏曰:古之人君,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;古之人臣,亦必度力度德而後居其任。雖百工胥史,且猶不茍,況三公乎?為君不明於所擇,為臣不審於自擇,以至亡身危主,誤國(guó)亂天下,皆由不勝任之故,可不戒哉!
○誠(chéng)齋楊氏曰:聖人亦豈責(zé)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,皆知大而不小,皆力多而不少哉?亦責(zé)其貪位而不量,已過(guò)分而不勝任,以至覆人之餗,敗己之身爾。
子曰:知幾其神乎!君子上交不諂,下交不瀆,其知幾乎!幾者,動(dòng)之微,吉之先見(jiàn)者也。君子見(jiàn)幾而作,不俟終日。易曰:介于石,不終日,貞吉。介如石焉,寧用終日,斷可識(shí)矣。君子知微知彰,知柔知?jiǎng)偅f(wàn)夫之望。
【先見(jiàn)之見(jiàn),賢遍反】。
○程子曰:先見(jiàn)則吉可知,不見(jiàn)則致兇。見(jiàn)幾而作,不俟終日,智之圓也。介如石,理素定也。理索定,故見(jiàn)幾而作,何俟終日哉!】
《本義》:此釋豫六二爻義。漢書(shū)吉之之間有兇字。
○朱子曰:知幾其神乎!便是這事難。如邦有道,危言危行;邦無(wú)道,危行言遜。今有一様人,其爽顗者又言過(guò)於直,其畏謹(jǐn)者又縮做一團(tuán),更不敢做事說(shuō)話,此便是曉不得那幾。若知幾,則自中節(jié),無(wú)此疚矣。君子上交不諂,下交不瀆。蓋上交貴於恭遜,恭則便近於諂;下交貴於和易,和則便近於瀆。蓋恭與諂相近,和與瀆相近,只爭(zhēng)些子,便至于流也。又曰:上交近於諂,下交近於瀆,如此當(dāng)知幾。纔過(guò)些子,便不是知幾。周子所謂幾善惡者,此也。又曰:君子上交不諂,下交不瀆。他這下而說(shuō)幾,最要看箇幾字,只爭(zhēng)些子。凡事未至而空說(shuō),道理易見(jiàn);事已至而顯然,道理也易見(jiàn)。唯事之方萌而動(dòng)之微處,此最難見(jiàn)。問(wèn):幾者動(dòng)之微,何以獨(dú)於上下交言之?曰:上交要恭遜,纔恭遜,便不知不覺(jué)有箇諂底意思在裏頭。下交不瀆,亦是如此。所謂幾者,只纔覺(jué)得近諂近瀆,便匆令如此,便是知幾。幾者動(dòng)之微,吉之先見(jiàn)者也。漢書(shū)引此句,吉下有兇字,當(dāng)有兇字。又曰:凡人上交必有些小取奉底心,下交必有些小簡(jiǎn)傲底心,所爭(zhēng)又只是些子。能如此而察之,非知幾者莫能。又曰:幾者動(dòng)之微,是欲動(dòng)未動(dòng)之間,便有善惡,便須就這處理會(huì)。若到發(fā)出處,更怎生奈何得?所以聖賢說(shuō)謹(jǐn)獨(dú),便都是要就幾微處理會(huì)。
○知微、知彰、知柔、知?jiǎng)偅撬募隆?/p>
○問(wèn):知微、知彰、知柔、知?jiǎng)偅链ㄗ饕?jiàn)微則知彰矣,見(jiàn)柔則知?jiǎng)傄樱湔f(shuō)如何?曰:也好。看來(lái)只作四體事,亦自好。既知微,又知彰;既知柔,又知?jiǎng)偅云錈o(wú)所不知,所以為萬(wàn)民之望也。
○張子曰:幾者,象見(jiàn)而未形者也。形則涉乎明,不待神而後知也。吉之先見(jiàn)云者,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。
○漢上朱氏曰:神難言也,精義入神,其唯知幾乎!知幾其神矣。幾者動(dòng)之微,吉之先見(jiàn)者也。譬如陽(yáng)生而井溫,雨降而雲(yún)出,衆(zhòng)人不識(shí),而君子見(jiàn)之。
○誠(chéng)齋楊氏曰:夫石者,至靜而無(wú)欲,至重而不動(dòng)者也。今也君子介然如石,天下之可欲者,何物能動(dòng)之乎?其見(jiàn)幾,寧用終日而後識(shí)之乎?
○雙湖胡氏曰:豫六二爻,唯曰介于石,不終日,貞吉,而夫子發(fā)明幾學(xué)以教人。蓋介有幾義,倪寛謂至纖至細(xì)處者,深為得之。上交謂五,下交謂初,唯當(dāng)豫時(shí),不諂不瀆,不沉溺於豫,此其所以為知幾也。
○臨川吳氏曰:穆生得免申、白之禍者,能見(jiàn)幾而作也。劉、柳竟陷伾、文之黨者,不能見(jiàn)幾而作也。
子曰:顔氏之子,其殆庶幾乎!有不善未嘗不知,知之未嘗復(fù)行也。易曰:不遠(yuǎn)復(fù),無(wú)祗悔,元吉。
【復(fù)行之。復(fù),扶又反】。
《本義》:殆,危也。庶幾,近意,言近道也。此釋復(fù)初九爻義。
○朱子曰:其殆庶幾乎!殆是幾字之義。又曰:是近義。又曰:殆是危殆者,是爭(zhēng)些子底意思。或以幾為因上文幾字而言,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,都只做近字說(shuō)。
○顏?zhàn)佑胁簧莆磭L不知,知之未嘗復(fù)行。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(fù)行為難,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。今人亦有說(shuō)道知得這箇道理,及事到面前,又卻只隨私欲做將去,前所知者都自忘了,只為是不曾知有不善未嘗不知,知之未嘗復(fù)行。直是顔子天資好,如至清之水,纖芥必見(jiàn)。
○李氏椿年曰:聖人無(wú)不善,賢人則容有不善,但未嘗不知,知之未嘗復(fù)行也。
○臨川吳氏曰:程子云:顔子無(wú)形顯之過(guò),夫子謂其庶幾未能不勉而中,所欲不踰矩,是有過(guò)也。然其明而剛,故一有不善,未嘗不知;既知,未嘗不遽改,乃不遠(yuǎn)復(fù)也。過(guò)既未形而改,何悔之有?復(fù)者,陽(yáng)反來(lái)復(fù)也。陽(yáng),君子之道,故復(fù)為反善之義。初,陽(yáng)來(lái)復(fù),處卦之初,復(fù)之最先,不遠(yuǎn)而復(fù)者也。失而後有復(fù),唯失之不遠(yuǎn)而復(fù),則不至于悔也。
天地絪緼,萬(wàn)物化醇;男女構(gòu)精,萬(wàn)物化生。易曰:三人行則損一人,一人行則得其友。言致一也。
【絪,音因。縕,紓云反】。
《本義》:絪縕,交密之狀。醇,謂厚而凝也,言氣化者也。化生,形化者也。此釋損六三爻義。
○朱子曰:天地絪縕,言氣化也;男女構(gòu)精,言形化也。致一,專(zhuān)一也。唯專(zhuān)一,所以能絪緼;若不專(zhuān)一,則各自相離矣。化醇,是已化後。化生,指氣化而言,草木是也。
○天地男女都是兩箇,方得專(zhuān)一;若三箇,便亂了。三人行,滅了一箇,則是兩箇便專(zhuān)一;一人行,得其友,成兩箇便專(zhuān)一。程子說(shuō)初與二,三與上,四與五,皆兩相與,自說(shuō)得好。
○臨川吳氏曰:絪緼者,氣之交也;構(gòu)精者,形之交也。天地之二氣交,故物之以氣化者,其氣醲厚而能醇;男女之二氣交,故物之以形化者,其精凝聚而能生。此氣形之相交以二,與三人損一,一人得友之相合以二者,其理同,皆言其以一合一,故能致一而不二也。
○漢上朱氏曰:天地萬(wàn)物,其本一也。天地升降,其氣絪緼,萬(wàn)物化矣。醇而未離,言其一而未始離也。天地既生萬(wàn)物,萬(wàn)物各有隂陽(yáng),精氣相交,化生無(wú)窮。男女曰化生者,言有兩則有一也。
○建安丘氏曰:損自泰來(lái),以未成卦言之,下乾為天,上坤為地,以乾上三爻交坤下三爻而為損,有天地絪緼之象。以既成卦言之,上坤變艮,艮為少男,下乾變兌,兌為少女,有男女構(gòu)精之象。
○張子曰:虛則受,盈則虧,隂陽(yáng)之義也。故隂得陽(yáng)則為益,以其虛也。陽(yáng)得隂則為損,以其盈也。艮三索而得男,乾道之所以成也。兌三索而得女,坤道之所以成也。故三之於上,則有天地絪緼,男女構(gòu)精之義。
子曰:君子安其身而後動(dòng),易其心而後語(yǔ),定其交而後求。君子修此三者,故全也。危以動(dòng),則民不與也;懼以語(yǔ),則民不應(yīng)也;無(wú)交而求,則民不與也。莫之與,則傷之者至矣。易曰:莫益之,或擊之,立心勿恆,兇。
【易其之易,以?反】。
《本義》:此釋益上九爻義。
○朱子曰:心平氣和則能言。易其心而後語(yǔ),謂平易其心而後語(yǔ)也。
○上下繫說(shuō),許多爻直如此分明。他人如說(shuō)得分明,便淺近;聖人說(shuō)來(lái)卻不淺近,有含蓄,所以分在上下繫也。無(wú)甚意義,是聖人偶去這處說(shuō),又去那處說(shuō)爾。
○融堂錢(qián)氏曰:安其身,易其心,定其交,非立心有恒者不能。然立心有恒,種種周密,缺一便不謂全。
○平庵項(xiàng)氏曰:危以動(dòng)則民不與者,黨與之與也;無(wú)交而求則民不與者,取與之與也。
○柴氏中行曰:身順道則安,悖道則危。心無(wú)險(xiǎn)陂則易,有險(xiǎn)陂則懼。以義相與為交定,以利相與為無(wú)交。動(dòng)而與,語(yǔ)而應(yīng),求而與者,物我一心而無(wú)間之者也。小人反是,獨(dú)言莫之與,則傷之者至矣,以益之上九專(zhuān)利自益故也。
右第五章。
雙湖胡氏曰:夫子於繫辭上傳既舉七卦爻辭以發(fā)明易道,今於此章復(fù)舉十卦十一爻之辭以論之。看來(lái)亦只是隨一時(shí)意之所欲言者則舉之,逐爻各自有意義,皆是為學(xué)者取法,未必先立主意,卻以卦實(shí)之也。
○雲(yún)峰胡氏曰:上繫七爻,下繫十一爻,皆象傳之文言也。學(xué)易者可觸類(lèi)而通其餘矣。
系辭下傳?第六章
子曰:乾坤,其易之門(mén)邪?乾,陽(yáng)物也;坤,隂物也。隂陽(yáng)合德,而剛?cè)嵊畜w。以體天地之撰,以通神明之德。
【撰,仕勉反】。
○程子曰:或曰:乾坤,易之門(mén),其義難知,餘卦則易知也。曰:乾坤,天地也。萬(wàn)物烏有出天地之外者乎?知道者統(tǒng)之,有宗則然也。而在卦觀之,乾坤之道簡(jiǎn)易,故其辭平直。餘卦隨時(shí)應(yīng)變,取舍無(wú)當(dāng),至為難知也。知乾坤之道者,以為易則可也。
《本義》:諸卦剛?cè)嶂w,皆以乾坤合德而成,故曰乾坤易之門(mén)。撰,猶事也。
○朱子曰:乾坤易之門(mén),不是乾坤外別有易,只易便是乾坤,乾坤便是易。似那兩扇門(mén)相似,一扇開(kāi)便一扇閉,只是一箇隂陽(yáng)做底。如闔戶謂之坤,闢戶謂之乾。
○問(wèn):門(mén)者,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,如兩儀生四象,只管生出,故曰門(mén)邪?為復(fù)是取闔闢之義邪?曰:只是取闔闢之義。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隂陽(yáng)闔闢而成。但看他下文云:乾,陽(yáng)物也;坤,隂物也。隂陽(yáng)合德,而剛?cè)嵊畜w。便見(jiàn)得只是這兩箇。
○乾,陽(yáng)物;坤,隂物。隂陽(yáng)形而下者,乾坤形而上者。天地之撰,即是說(shuō)他做處。
○進(jìn)齋徐氏曰:陽(yáng)畫(huà)為乾,隂畫(huà)為坤。門(mén),猶闔戶、闢戶之義。一闔一闢,為易之門(mén),其變無(wú)窮,皆二物也。隂陽(yáng)合德,謂二物交錯(cuò)而相得有合。剛?cè)嵊畜w,謂成卦爻之體也。天地之撰,隂陽(yáng)造化之跡也。有形可擬,故曰體。體天地之撰,言聖人作易,皆以體法造化之事,而效其至著者也。神明之德,隂陽(yáng)健順之性也。有理可推,故曰通。通神明之德,言易畫(huà)既作,又以通知造化之理,而極於至微者也。又曰:自形而上者言之,故先隂而後陽(yáng)。自形而下者言之,故先剛而後柔。
○凌氏曰:乾坤物於隂陽(yáng),而由隂陽(yáng)以闔闢,故曰:乾,陽(yáng)物也。坤,隂物也。
○節(jié)齋蔡氏曰:乾坤合而後成衆(zhòng)卦爻之體,如剛來(lái)而下柔,剛上而柔下,此類(lèi)皆由乾坤相合而成,所謂隂陽(yáng)合德而剛?cè)嵊畜w也。
○雲(yún)峰胡氏曰:其初也,隂陽(yáng)分而為兩儀,隂陽(yáng)之合則為四象八卦,而剛?cè)犰妒呛跤畜w。著而天地之撰,微而神明之德,皆自乾開(kāi)其始,而坤成其終,故曰:乾坤,易之門(mén)。
其稱(chēng)名也,雜而不越,於稽其類(lèi),其衰世之意邪?
《本義》:萬(wàn)物雖多,無(wú)不出於隂陽(yáng)之變,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繆。然非上古淳質(zhì)之時(shí)思慮所及也,故以為衰世之意。蓋指文王與紂之時(shí)也。
《或問(wèn)》:其稱(chēng)名也,雜而不越,是指繫辭而言?是指卦名而言?
○朱子曰:他後面兩三番說(shuō)名,後又舉九卦說(shuō),看來(lái)只是謂卦名。
○問(wèn)於稽其類(lèi)。曰:但不過(guò)是說(shuō)稽攷其事類(lèi)。
○其衰世之意邪?伏羲畫(huà)卦時(shí),這般事都已有了,只是未曾經(jīng)歷。到文王時(shí),世變不好,古來(lái)未曾有底事都有了,他一一經(jīng)歷這崎嶇萬(wàn)變過(guò)來(lái),所以說(shuō)出那卦辭。如箕子之明夷,如入于左腹,獲明夷之心于出門(mén)庭,此若不是經(jīng)歷,如何說(shuō)?
○雲(yún)峰胡氏曰:伏羲三畫(huà)卦名,自乾一至坤八,有自然之序,因而重之亦然。至文王稱(chēng)卦之名則雜,而非復(fù)伏羲之序矣。然其稱(chēng)名雖雜,而於伏義之易未嘗差違。稽類(lèi)考占,世之衰也,蓋有不得不然者矣。
○柴氏中行曰:乾坤足以盡天下之道,萬(wàn)物由之足矣,何用不一之名?世衰道微,人之情偽滋熾,聖人不得不明其道以示天下。
○進(jìn)齋徐氏曰:上古之世,俗樸民淳,迷於吉兇之塗,而莫知所趨。故伏羲畫(huà)卦以教之占,而吉兇以明,斯民由之而無(wú)疑也。雖乾陽(yáng)坤隂,剛?cè)峤诲e(cuò),顯而體天地之撰,微而通神明之德,然剛勝則吉,柔勝則兇,亦未嘗費(fèi)辭也。中古以來(lái),人心變?cè)p,迷謬愈甚。文王、周公於是繫卦爻之辭,稱(chēng)名辨物,稽類(lèi)考占,以開(kāi)示隂陽(yáng)之義。易之道雖無(wú)餘藴,而聖人憂患後世之意,蓋亦有不得已然者,故下文又申言之。
夫易,彰往而察來(lái),而微顯闡幽,開(kāi)而當(dāng)名辨物,正言斷辭,則備矣。
【夫,音扶。當(dāng),去聲。斷,丁亂反】。
《本義》而微顯,恐當(dāng)作微顯而。開(kāi)而之而,亦疑有誤。
○朱子曰:彰往察來(lái),往者如隂陽(yáng)消長(zhǎng),來(lái)者事之未來(lái)吉兇。問(wèn):彰往察來(lái),如神以知來(lái),知以藏往相似,往是已定。?如天地隂陽(yáng)之變,皆已見(jiàn)在只卦上了。來(lái)謂方來(lái)之變,亦皆在這上。曰:是。
○微顯闡幽,幽者不可見(jiàn),便就這顯處說(shuō)出來(lái)。顯者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(jiàn)底,教人知得如此顯。道神德行相似,德行顯然可見(jiàn)者,道不可見(jiàn)者。微顯闡幽,是將道來(lái)事上看,言那箇雖是粗底,然皆出於道義之藴。微顯所以闡幽,闡幽所以微顯,只是一箇物事。
○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。
○進(jìn)齋徐氏曰:往謂隂陽(yáng)消長(zhǎng),剛?cè)嶙兓载乘卣撸捉灾髦试徽猛?lái)謂吉兇未定,事之方來(lái)者,占筮中所告,可以前知,故曰察來(lái)。顯者,微之使求其原,故曰微顯。幽者,闡之使見(jiàn)其端,故曰闡幽。當(dāng)名,謂父子君臣之分,貴賤上下之等,各當(dāng)其位也。辨物,謂乾馬、坤牛、離火、坎水、碩果、莧陸之類(lèi),悉辨其似也。正言,謂元亨利貞,直方大之辭,正其言以曉人也。斷辭,謂利涉大川,不利涉大川,可小事,不可大事之語(yǔ),有以決其疑也。
○雲(yún)峰胡氏曰:辨物、正言、斷辭,後天之易也,視先天則為備矣。
○臨川吳氏曰:彰往,即藏往也,謂明於天之道,而彰明已往之理。察來(lái),即知來(lái)也,謂察於民之故,而察知未來(lái)之事。微顯,即神德行也,謂以人事之顯,而本之於天道,所以微其顯。闡者,闢而顯之也。闡幽,即顯道也,謂以天道之幽,而用之於人事,所以闡其幽。上篇之藏往、知來(lái)、顯道、神德行,兼蓍而言,此則專(zhuān)以卦而言也。
其稱(chēng)名也小,其取類(lèi)也大。其旨遠(yuǎn),其辭文,其言曲而中,其事肆而隱。因貳以濟(jì)民行,以明失得之報(bào)。
【中,丁仲反。行,下孟反】。
《本義》:肆,陳也。貳,疑也。
進(jìn)齋徐氏曰:負(fù)乘往來(lái),事名之小者也。茅棘豕雉,物名之小者也。所稱(chēng)雖小,而其所取之類(lèi),皆本於隂陽(yáng),非稱(chēng)名也,小取類(lèi)也。大乎旨,謂所示之理。文,謂經(jīng)緯錯(cuò)綜也。極天下之賾,凡天地隂陽(yáng)、道德性命之奧象皆示之,而其所繫之辭,經(jīng)緯錯(cuò)綜,皆有自然之文,非其旨遠(yuǎn),其辭文乎?曲,委曲也。凡委曲其文者,未必皆中乎理,易則言雖曲而無(wú)不中也。肆,陳也。凡敷陳其事者,無(wú)
上一章節(jié)
下一章節(jié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