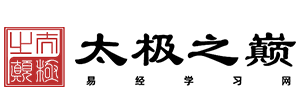【周易上經(jīng)】第13卦-同人?天火同人(離下乾上)-[明]釋智旭撰《周易禪解?卷三》

同人。于野亨。利涉大川。利君子貞。
約世道。則傾否必與人同心協(xié)力。約佛法。則因犯結(jié)制之后。同法者同受持。約觀心。則既離順道法愛。初入同生性。上合諸佛慈力。下同眾生悲仰。故曰同人。蘇眉山曰。野者。無求之地。立于無求之地。則凡從我者皆誠同也。彼非誠同。而能從我于野哉。同人而不得其誠同。可謂同人乎。故天與火同人。物之能同于天者蓋寡矣。天非同于物。非求不同于物也。立乎上。而能同者自至焉。其不能者不至也。至者非我援之。不至者非我拒之。不拒不援。是以得其誠同而可以涉川也。茍不得其誠同。與之居安則合。與之涉川則潰矣。觀心釋者。野是三界之外。又寂光無障礙境也。既出生死。宜還涉生死大川以度眾生。惟以佛知佛見示悟眾生。名為利君子貞。
彖曰。同人。柔得位得中。而應(yīng)乎乾。曰同人。(蘇眉山曰。此專言二。)同人曰。同人于野亨。(蘇眉山曰。此言五也。故別之。)利涉大川。乾行也。文明以健。中正而應(yīng)。君子正也。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。
觀心釋者。本在凡夫。未證法身。名之為柔。今得入正位。得證中道。遂與諸佛法身乾健之體相應(yīng)。故曰同人。此直以同證佛性為同人也。既證佛體。必行佛德以度眾生。名為乾行。文明以健。中正而應(yīng)。如日月麗天。清水則影自印現(xiàn)。乃君子之正也。惟君子已斷無明。得法身中道。應(yīng)本具二十五王三昧。故能通天下之志。而下合一切眾生。與諸眾生同悲仰耳。
象曰。天與火。同人。君子以類族辨物。
不有其異。安顯其同。使異者不失其為異。則同乃得安于大同矣。佛法釋者。如天之與火。同而不同。不同而同。十法界各有其族。各為一物。而惟是一心。一心具足十界。十界互具。便有百界千如之異。而百界千如究竟元只一心。此同而不同不同而同之極致也。
周易禪解卷三:同人初九
初九:同人于門。無咎。象曰。出門同人。又誰咎也。
同人之道。宜公而不宜私。初九剛正。上無系應(yīng)。出門則可以至于野矣。故無咎。
周易禪解卷三:同人六二
六二。同人于宗。吝。象曰。同人于宗。吝道也。
六二得位得中以應(yīng)乎乾。卦之所以為同人者也。然以陰柔不能遠(yuǎn)達(dá)。恐其近匿于初九九三之宗。則吝矣。
周易禪解卷三:同人九三
九三。伏戎于莽。升其高陵。三歲不興。象曰。伏戎于莽。敵剛也。三歲不興。安行也。
夫二應(yīng)于五。非九三所得強(qiáng)同也。三乃妄冀其同。故伏戎以邀之。升高陵以伺之。然九五陽剛中正。名義俱順。豈九三非理之剛所能敵哉。其。即指三。高陵指五。五遠(yuǎn)于三。如高陵也。
周易禪解卷三:九四
九四。乘其墉。弗克攻。吉。象曰。乘其墉。義弗克也。其吉。則困而反則也。
離象為墉。四亦妄冀同于六二。故欲乘九三之墉以下攻之。但以義揆。知必取困。故能反則而弗攻耳。
周易禪解卷三:同人九五
九五:同人先號(hào)啕而后笑。大師克相遇。象曰。同人之先。以中直也。大師相遇。言相克也。
六二陰柔中正。為離之主。應(yīng)于九五。此所謂不同而同。乃其誠同者也。誠同而為三四所隔。能弗號(hào)啕而用大師相克哉。中故與二相契。而不疑其跡。直。故號(hào)啕用師而不以為諱。鄭孩如曰。大師之克。非克三四也。克吾心之三四也。私意一起于中。君子隔九閽矣。甚矣。克己之難也。非用大師。其將能乎。楊誠齋曰。師莫大于君心。而兵革為小。
周易禪解卷三:同人上九
上九:同人于郊。無悔。象曰。同人于郊。志未得也。
蘇眉山曰。無所茍同。故無悔。莫與共立。故志未得。觀心釋者。六爻皆重明欲證同人之功夫也。夫欲證入同人法性。須藉定慧之力。又復(fù)不可以有心求。不可以無心得。所謂時(shí)節(jié)若到。其理自彰。此修心者勿忘勿助之要訣也。初九正慧現(xiàn)前。不勞功力。便能出生死門。六二雖有正定。慧力太微。未免被禪所牽。不出三界舊宗。九三偏用其慧。雖云得正。而居離之上。毫無定水所資。故如升于高陵。而為頂墮菩薩。三歲不興。九四定慧均調(diào)。始雖有期必之心。后乃知期必之不能合道。卒以無心契入而吉。九五剛健中正。而定力不足。雖見佛性。而不了了。所以先須具修眾行。積集菩提資糧。藉萬善之力。而后開發(fā)正道。蓋是直緣中道佛性。以為回出二諦之外。所以先號(hào)啕而后笑也。上九定慧雖復(fù)平等。而居乾體之上。僅取涅槃空證。不能入廛垂手。故志未得。